摘要:文章以北京市昌平區香堂村、下苑村為例,通過入戶問卷調查及數據統計分析,對京郊宅基地流轉的現狀、效益及問題進行了研究。研究發現,京郊宅基地流轉的形式以出租和買賣為主,宅基地出租多沿村莊道路集中分布;宅基地買賣表現為地上房屋的買賣,出售后房屋閑置現象突出;宅基地置換導致老宅基地廢棄,置換后的建筑空間對村莊布局產生影響;流轉后使用主體以非村民為主,房屋功能以居住、商用為主。宅基地流轉帶來了一定的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主要表現在:農村集體獲益,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增加;吸納流動人口,城鄉資源有效互補;促進土地節約集約利用,緩解中心城區土地供給壓力。與此同時也衍生出一系列問題,主要表現在隱形流轉多暗箱操作,缺乏產權保障;無序置換及收益分配不完善,導致村民生活水平差異較大;無序的宅基地流轉影響村莊空間發展。
關鍵詞:宅基地流轉;宅基地利用;北京市近郊區;香堂村;下苑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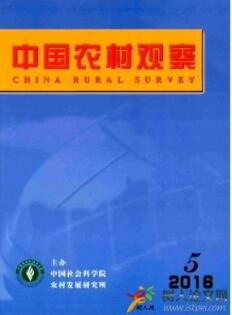
《中國農村觀察》(雙月刊)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主辦的專業理論刊物。探討中國農業改革與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反映該領域研究的前沿成果,注重文章的實證性和資料性,提倡學術觀點的爭鳴。
引言
在快速城市化推動和市場經濟體制作用下,宅基地進入土地市場隱形流轉已成為普遍現象。北京郊區大部分村鎮的宅基地流轉案例占宅基地總數的10%左右,有的甚至高達40%以上,且多分布在交通便利、工業基礎條件優越、遠郊平原景觀秀麗的區域[1]。在我國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農村宅基地的利用問題引起了政府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國發〔2004〕28號)、“十二五”規劃綱要和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相繼提出要加強農村宅基地的管理,完善農村宅基地管理機制,進一步促進農村宅基地的節約集約利用,切實保護農民宅基地的合法權益。學術界對宅基地問題的研究涉及法學、社會學、管理學、地理學及城市規劃等多學科,對宅基地流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宅基地流轉的現狀[2]、社會經濟法律制約[3]、制度創新[4]等內容,涉及流轉機制、驅動力[5]、阻礙因素、意愿分析及制度與模式探討[6-7]等多方面,但從微觀個案出發對宅基地流轉問題進行實證研究的較少。北京市的城市擴張,尤其是以住宅建設為主導的空間擴張正逐漸向西北淺山地區蔓延[8],宅基地流轉現象也已由近郊向遠郊擴展。深入了解該區域內的宅基地流轉現狀與問題,有助于引導其健康有序發展,促進宅基地的集約節約利用。
香堂村、下苑村均位于北京近郊區,受城市擴張影響,宅基地流轉現象較多。香堂村位于昌平區崔村鎮東部,是京郊以“小產權房”而聞名的村莊。下苑村位于昌平區興壽鎮東部,是京郊著名的畫家村。本文以香堂村和下苑村為例,對京郊宅基地流轉現狀進行評價。
1 北京近郊農村宅基地流轉現狀
1.1?宅基地以出租為主,因商用而出租的現象多沿道路集中分布
出租是宅基地流轉較為普遍的形式,即村民在依法取得的宅基地上建成房屋后,將房屋整體或部分出租,個人獲得利益,承租人將其作為住宅、辦公、休閑、倉庫或其他經營服務場所,在出租房屋的同時也出租了宅基地的使用權 [9]。從出租形式來看,兩村均以部分房屋出租為主,香堂村整院出租的比例為35.3%,下苑村為11.1%。房屋出租年限與出租后功能相關。整院出租的房屋租期均為1年以上;部分院落出租的房屋,用于商用的房屋租期多為1年以上,而用于居住的多為1年以下短租或不定期出租。整院出租多為隨機分布,未表現出明顯的空間分布特點;部分房屋出租多集中分布在村莊道路兩側,這種空間分布特點與房屋出租后的功能有關。整院出租的房屋主要用于居住,房屋區位因素影響小,主要影響因素為房屋的新舊程度、基礎設施和價格等。部分出租的房屋主要為商用,沿道路兩側的東西廂房具有較好的區位優勢,承擔了門面房的作用,為承租者的經營提供了有利條件。
1.2?宅基地買賣表現為地上房屋的買賣,出售后房屋閑置現象突出
宅基地買賣主要表現為地上房屋的買賣,宅基地使用權在房屋交易過程中發生轉移。香堂村宅基地買賣比例高達35.8%,交易多發生在村集體與城鎮居民之間,房屋類型為村集體在2002—2010年開發建設的三合院,主要位于居民點的中北部。據調查,北區124套絕大多數都已售出。在調研到的34處已售房屋中,處于閑置狀態的有18處。房屋賣出后的利用現狀與購房目的有關。正在使用中的宅基地,購房者多為北京市城鎮退休居民,因香堂村具有較好的區位和環境條件,為養老居住在此購房。而閑置的宅基地,購房者多以投資房地產為目的,將其作為資產增殖的重要手段,并未真正入住。
1.3宅基地置換導致老宅基地廢棄,置換后的建筑空間對村莊布局產生影響
宅基地置換是香堂村宅基地流轉的一種特殊形式。根據置換是否需要繳納現金,可分為無償置換和有償置換。無償置換多由于村集體進行基礎設施或房地產開發建設需占用村民宅基地而發生,置換后村民自己出資建房或繼續沿用其他村民的房屋。無償置換具有集體占地補償的性質,且雙方在置換過程中均未獲取土地收益,置換前后宅基地使用主體發生變化。有償置換指由村集體主導進行房地產開發建設,將統一建好的一定面積的房屋有償分給村民,意愿置換的村民將舊房和老宅基地作價,補交剩余款項,換取新宅基地或樓房。
根據置換后的地上建筑形式劃分,可分為宅基地換普通民居、宅基地換樓房和宅基地換三合院(見表1)。宅基地換普通民居多為無償置換,少數有償置換的現象主要依據置換后宅基地面積增大及房屋較新交納現金補貼。后兩類均為有償置換。宅基地換樓房集中在2004年、2005年和2009年。村民樓房共10棟,共有400戶家庭入住。宅基地換三合院集中在2002年,村集體以舊村改造的名義在農村居民點南部集中建設100套三合院,以有償置換的形式將老村中的100戶村民遷出,導致老宅基地廢棄。2002年之后,村集體陸續利用村內存量和廢棄宅基地在農村居民點北部建設124戶三合院,除供給村民用以宅基地置換外,也面向城鎮居民出售。宅基地置換現象對村莊肌理、建筑密度及交往空間產生了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村民的生產生活方式。
1.4?流轉后使用主體以非村民為主,房屋功能以居住、商用為主
農村宅基地的使用主體可分為村集體、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村民)和非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非村民)三類。農村宅基地流轉不僅包括宅基地使用主體的變化,也包括地上房屋的功能變化。房屋的使用功能分為居住、商用和閑置。從流轉形式來看,部分房屋出租最有可能導致房屋功能的改變。
在香堂村,宅基地出租后使用主體多由本村村民轉為京外務工人員。整院出租中,承租者均為外地人,多從事建筑施工及裝修等工作。部分房屋出租中,承租者除多為外來打工者外,主要從事副食及餐飲零售行業。香堂村宅基地買賣多由村集體主導,買賣后使用主體由村集體流轉為北京城鎮居民。在置換過程中,宅基地使用主體在本村村民之間或村民與村集體之間轉移。置換后,村民的老宅基地成為村集體“小產權房”開發建設用地,待房屋建成售出之后,宅基地的使用主體再由村集體流轉給非本村村民。有17.6%的房屋功能發生了轉變,由單純的居住功能流轉為“居住+商用”功能。在商業經營類別上,多為與村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服務業,包括餐飲、洗衣、復印店及旅游接待等。
在下苑村,宅基地出租后使用主體多由本村村民轉為學生,少數為畫家、雕塑家等自由職業者。下苑村的宅基地買賣多為村民個人行為,宅基地使用權由本村村民流轉為畫家及京外務工人員。下苑村部分房屋出租后,出現了房屋閑置的情況。這是由于藝術學校生源的減少,導致房屋出租率下降,原本具有出租房的家庭開始出現閑置現象。
2 北京近郊農村宅基地流轉效益
2.1?經濟效益:農村集體獲益,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增加
房屋出租價格依據出租房屋數量、房屋新舊程度和房屋用途而有所不同。整院出租多按年支付,房屋質量越好,價格越高。香堂村三合院的年租金在3萬元左右,而普通民居的租金僅7000~8000元。部分房屋出租多按月支付,租住的單間每月150~300元,從事副食零售等行業的沿街房屋每月均價在每間200~400元,從事建材零售行業的沿街房屋租金較高,在600~800元。房屋出租增加了農民的財產性收入。通過宅基地流轉,村民將閑置的房屋變為現金收入的來源。這對于賦閑在家的老年人更為重要,收入可作為其養老支出的一部分。房屋出租的家庭中,家庭年收入從10000元到45000元不等,租金收入占家庭年收入比例由7.5%到26.9%不等,這一比例超過15%的家庭數量占70%以上,說明房屋出租的確成為了村民收入的重要來源。
此外,香堂村的宅基地換房舉措改善了一部分村民的居住和生活環境,解決了部分低收入村民無能力建房的問題。被置換和整合后的原宅基地統一開發建設為樓房或三合院,村集體通過對“小產權房”買賣獲取大量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集體致富。2011年,香堂村三合院的售價為150萬元,二合院的售價為100萬元,而其建造成本約30萬元。目前,村內建成的三合院已全部售出。2010年香堂村進行了農村土地股份確權,村民根據不同情況獲得一定數量的土地股、戶籍股、勞齡股、獨生子女股等股份,村民每年可按此分享村集體的土地所得收益。
2.2?社會效益:吸納流動人口,城鄉資源有效互補
宅基地的出租容納了大量的流動人口,減少了城市建設成本。由于香堂村一直以來進行“小產權房”開發建設,村內從事建材批發、建筑施工、裝修、餐飲零售等二、三產業的流動人口約有3000人。由于租住民宅的費用低廉,大部分務工者、小商小販居住在民宅中,下苑村的出租房也成為學生的主要住房保障。宅基地流轉特別是宅基地出租減輕了地方政府和社會的壓力,也降低了城市各項建設的人力成本。
宅基地流轉可以調節農民的房屋余缺,緩解無房戶的急需,特別是在宅基地審批凍結時期,村民購買閑置宅基地,有利于宅基地的節約利用。農民進城就業居住后的閑置房屋,被城鎮居民購買用于養老或度假居住,也是城鄉資源互補的一種體現。
2.3?生態效益:促進土地節約集約利用,緩解中心城區土地供給壓力
香堂村以“宅基地置換”為主的流轉形式促進了農村居住空間的轉型,使村民由平房上樓,促進了土地的節約集約利用,帶來了生態和經濟雙重效益。由于香堂村大多數村民已從事第三產業,從業形式的轉變也逐漸影響了居民的生活方式。大面積的農村居民點土地利用效率低,以宅基地換樓房的形式使有意愿的農民上樓,有助于土地的整理與開發。同時,村集體開發的樓房也吸引了部分城鎮居民前來購房,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心城區土地的供給壓力。
3 北京近郊農村宅基地流轉衍生問題
3.1?隱形流轉多暗箱操作,缺乏產權保障
由于我國法律對農村宅基地流轉的限制,導致農村住房和宅基地不能進入市場流轉,宅基地流轉處于非法或地下、半地下狀態。宅基地出租多為自發流轉、靈活性大、交易便捷,但絕大多數交易雙方只有口頭協議,沒有簽訂租房合同。宅基地買賣中,香堂村售樓處只有與業主簽訂的購房合同,無房產證。宅基地置換中,香堂村村民只有與村集體簽訂的置換協議,新宅基地并沒有使用許可證,村民持有的仍為20世紀80年代頒發的宅基地使用證。目前以自發流轉為特征的農村宅基地隱形市場,信息公開不充分,風險較大又難以監控,存在很多隱患,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缺乏產權的保障。交易雙方的權益無法保障,很容易產生交易糾紛。
3.2?無序置換及收益分配不完善,導致村民生活水平差異較大
香堂村的房屋開發建設缺乏長遠有效規劃,往往是“哪里有地,哪里蓋房”,“要占誰家的宅基地,誰家才能有機會換房”。這種情況導致了村民之間居住條件和生活環境的差異,進而導致村民生活水平的較大差異。宅基地無序置換,會造成個別不想換房的村民被動置換,想要置換的村民卻又沒有機會的不平等現象。另外,三合院區和老村基礎設施條件不同,前者集中供暖,后者卻沒有。位于老村部分的很多村民,由于沒有足夠資金建房,自家宅基地又沒有被劃入規劃范圍內,沒有置換資格,居住條件一直得不到改善,村民發展差距加大。
3.3?無序的宅基地流轉影響村莊空間發展
在香堂村,以村集體為主導進行的宅基地買賣與置換行為對村莊肌理的改變與影響最大。老村區域,宅基地與建筑布局受山地制約而自然順應地勢,形成由幾個不同高差的臺地條狀伸展布局為特點的條紋式村莊肌理。而舊村改造后的兵營式布局導致村落肌理單一,雖然節約用地、施工方便,但村落空間較為單調。而且在村落自然、文化與歷史背景下長期演化而成的彎曲的街巷、錯落的房屋及多變的空間都變成了單一線型空間,房前屋后各種大小不一的公共、半公共空間統一為集中的公共活動中心,原有村莊鄰里網絡結構也變得松散。建筑與宅院是村莊肌理演變中最主要的單元。分布在老村中的普通民居建筑形式多樣,建筑材料多取自于當地,為石頭和磚瓦,建筑依山勢而建,錯落有致。而在三合院區域,建筑均采用統一的尺度與形式,建筑材料均為磚木。村莊肌理細胞的多樣性變差,村莊肌理逐漸呈現出單一、大同的整體趨勢。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