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美貿易沖突總體表明中美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現在講中美關系,貿易方面的問題是冰山在海平面之上最直觀的部分,其實要同時全面考慮兩個大國之間的總體關系,必須把水面之下往往并不直接感受到的其他因素放在一起。以創新的機制擴張本土選擇性“有效投資”,應成為貿易摩擦升級新階段上我們“有所作為”的一大重點。除內部視角的這一重點之外,外部視角的重點,則是注重“多邊博弈”,爭取一切可調動潛力和有利因素,去應對中美間的“雙邊博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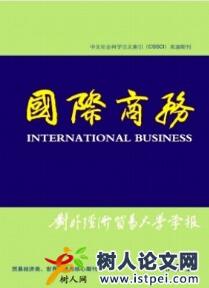
關鍵詞:中美貿易摩擦中美關系多邊博弈
一、基本判斷
中美貿易沖突總體表明的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中美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現在講中美關系,貿易這方面的問題是冰山在海平面之上最直觀的部分,其實要同時全面考慮兩個大國之間的總體關系,必須把水面之下往往并不直接感受到的其他因素,如制造業的實力、科技創新的能力,特別是金融方面的影響力、輻射力,終極設想情況之下的軍事對抗實力、勝算如何,以及不可忽視的全球化范圍內的軟實力等,放在一起。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可引出一個基本認識:中國遠遠沒有達到可以和美國在較量概念上去對決的平臺。
既然如此,我們就必須重新體會鄧小平同志當年具有很高戰略思維水平的“冷靜觀察,沉著應對,善于守拙,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為”這一相關大政方針的表述。現實情況下,這對于我們實際的戰略把握和策略要領可形成強有力的指導。筆者認為要有一個清醒判斷:就是美國現在已經朝野一致地形成了全面遏制中國的基本共識,無論特朗普能不能連任、在不在位,這個基本情況已不會有多大改變。換個人可能還更難受。
中美之間既然是貿易戰戰端已開,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將成為長期現象。這也合乎我們現在必須點破的:不論人類文明怎么發展,到了一定的臨界點之后,是叢林法則更多地來主導了。老大就是要遏制老二。中國的總量第二是伴隨著我們人均國民水平還相當低的情況,還沒有達到人均國民收入10000美元,到了10000美元再往上走,至少需要沖過13000美元,我們才能穩穩地坐在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上。
所以,未來的十年是非常關鍵的十年,而這關鍵的十年中,作為戰略博弈對方的美國,如果在以競爭為主、叢林法則的考慮之下,當然會強化遏制中國的意識和行為。這個十年的考驗期,對于中國來說不在于全面小康,因為全面小康懸念不大,關鍵就是能不能遏制我們自身的矛盾凸顯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對策建議
第一,變壞事為好事。貿易摩擦沖突肯定是壞事,我們現在已經感覺到市場的走低,一些指標向不良方面發展,但是確實也不應在沖擊下“應激反應”式高估實際影響。2018年度我國經濟已實現了6.6%的增長,經過努力,大概率是仍能在2019—2020年實現年均6%增速以上。這樣,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應該達到的保證速度是沒有問題的,再加上社會政策托底、精準扶貧等等,全面小康目標仍然可以兌現。
特別關鍵的是,要注意把可能調動起來的潛力與伴隨不良局面仍可能實現的一些好的方面抓住,使這些充分體現出來。比如我們已經明確宣布降低關稅,進口汽車原25%的關稅,如降到5%,一下削掉20個點。中國社會成員里很多人(我國中產階層有3億人以上)收入增長以后,想買國外的一些品牌車輛,這些社會成員不是得到實惠嗎?特別是藥品——李克強總理強調藥品的關稅下降,后面要跟著盯住它的實際價位。
幾十種治療癌癥的有效藥,過去老百姓輕易得不到,或者要以很高的代價去得到,現在藥價降低了,有癌癥病人的家庭馬上得到實惠。美國人現在于大豆方面受到我們施壓反制,國內東北生產大豆的農戶和農場員工及其這一加工鏈上的市場主體,便一下面臨著一個市場份額擴大的向好機遇。這些還是僅從局部來說的壞事變好事。其實對全社會來說,壞事變好事更加意義重大。我們應意識到,中國還要進一步開放。新的情況之下,我們可以觀察,在影視、互聯網等等方面,可以進一步開放。比如大家都知道谷歌學術搜索的水準高,很多在國外學習過的人,從那個外部環境回到國內,會因不能方便地運用谷歌學術搜索,而感到痛苦。政協的一位副主席曾經和其他一些專家聯名提交過提案,認為至少考慮谷歌的學術搜索應在國內放開,但沒有回音。
現在新的情況下,壞事變好事,是不是可以更積極地考慮這些事情。最為重要的是新局面下進一步擴大開放向“三零”靠近的“二次入世”,是“清理文件柜”,就是杜潤生同志當年表述的“這就是變法”,變法就是圖強、創新,這種全局性的好處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三零即“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應看到海南自由貿易港,已是我國實踐中要爭取的極致情況;從上海開始,已有三輪“復制”,以后還應繼續“可復制”的內陸眾多自由貿易區,自是其“中高端”形式。
第二,變壓力為動力。需承認我們是在壓力之下被動接招,我們的籌碼跟美國相比是不足的,貿易摩擦打到一定程度以后,人家還是用絕對數,我們就必須用相對數了。反制是必要的,但適當的反制還得尋求在妥協中間。能夠斗而不破,爭取新的平衡狀態。以戰促談、以戰促和,至少是階段性的平衡狀態。所謂“打打停停”,停的時候就是平衡,平衡又被突破就要打一打。新的階段上,爭取斗而不破的過程中,我們變壓力為動力,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我們能做的、自己主動選擇的,是堅定不移地在改革的深水區來沖破阻力攻堅克難,實現習總書記說的把硬骨頭啃下來。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這些年有這么多的改革文件,這么多的改革要求,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深改組會議強調進一步解放思想,“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工作再抓實”,然而實際生活中抓實的有多少?中央多次下文,重申允許改革犯錯誤,但不允許不改革,實際上誰敢在這方面有自己的創新?
如果一個人干事,好幾個人審查監督挑毛病,抓到任何毛病不說是改革中犯的錯誤,而是“心術不正”,把事情弄得“吃不了兜著走”。
這種情況下,有了壓力,我們是不是可以變成動力來沖一沖局面?鄧小平同志當年說要大膽試、大膽闖,現在誰敢闖?但至少要給出創新的試錯空間。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要在壓力之下進一步開放和倒逼改革。2019年3月中央下發《關于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主導精神是要敢擔當有作為做實事,力戒形式主義,使2019年成為“基層減負年”。
“粵港澳大灣區”加入區域發展戰略重點,十分值得稱道,實際上是使“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廣東、深圳與珠三角,更毅然決然去和港澳已具備的較成熟市場經濟的“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對標,打造未來可與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相媲美的強勁增長極。或大或小這方面可做的事情,如果排列起來,是一個長長的清單,是怎么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60條”的336項改革任務,以及后續我們認識清楚的另外一些改革任務,這是一個系統工程。
要承認,在這方面畢竟我們還是有進展的,比如近年的大部制改革,在十幾年的時間段以后,終于走出了相對像樣的步伐,要乘勢推進這種改革,對整個行政架構傷筋動骨式的做改造,減少局委辦,減少審批權。這后面,才能減少跟著派生出來的收費權、設租權,才能真正降低中國納稅人、企業所說的負擔。中國這個實際上的負擔絕對不是18種正稅所能概括的,“五險一金”在世界上確實是最高水平之列的,幾百種行政性收費更是非常過分的,克強總理說這是涉及“拆香火”的問題,“拆香火”那就是大部制加扁平化,一定要對整個行政架構做脫胎換骨的改造。如果能變壓力為動力,把這種開放和改革的實事堅定不移地做好,中國才有后勁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控制我們現在的矛盾凸顯,于化解矛盾中維持基本的穩定局面,實現中央說的“新兩步走”。
第三,逐步變被動為主動。中國現在追求的是“強起來”時代的升級發展,要形成發展的后勁,其實包含著的戰略取向,是必須繼續超常規地追趕,繼續大踏步跟上時代的步伐。速度狀態上從原來的兩位數落到6%左右,仍然是大經濟體里面的高速度(我們稱為“中高速”)。在質量提升的過程中,最關鍵的是我們怎么樣處理好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基本關系。鄧小平同志在“八九”之后美國帶頭“全面制裁”的局面中特別強調,從歷史長河來看,這是一場“小風波”,要繼續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搞好關系。我們現在還應有這個戰略思維:因為我們別無選擇,必須在這個“有理、有利、有節”的斗而不破的過程中,堅定不移地啃硬骨頭做好自己的事情,那么時間是中國最好的朋友。
如果我們能夠避免犯低級錯誤,把握好大的方向,給社會成員各個層面的創業創新者以安全感,給我們整個社會以預期之上的希望感,我們便能夠在已經有的幾十年發展成就基礎上,于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的過程中保持可持續性。1900年至2017年,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了36倍,而中國的GDP從改革開放后的80年代中后期到2017年,已經實現了36倍的成長,時間軸上中美之比是1:4。即中國人以1個時間單位實現了美國人4個時間單位的經濟成長性,很好體現了中國走對了現代化之路后的“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時間已是中國最好的朋友。如果我們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的局面就會比現在更明朗一些。現在面對這些不確定性,我們所能抓住的確定性歸根結底就是能選擇什么,我們一定要正確選擇進而做好可做、應做的“自己的事情”。
第四,多方協力增加選擇性“有效投資”。外部“大兵壓境”,內部亟需穩住“陣腳”,擴大內需。筆者有一條特別建議:多方協力增加選擇性“有效投資”,運用創新機制,形成中國以投資潛力、創新活力釋放帶出的巨大消費潛力,形成抵御美國方面不確定性不良影響的同時對自己確定性的充分把握,實現6%以上年均增速的高質量發展。具體有三點:一是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空間還相當巨大,有效投資可選項目俯拾皆是。投資概念下的供需互動,從各中心區軌道交通網、全國約5000萬個停車位、地下綜合管廊、海綿城市、天網天眼工程、污水垃圾循環利用、生態環境整治、鄉村振興新區和產業新城連片開發等等,做起來空間堪稱“可觀、可貴、可用”,各種要素皆備。相對應的公私合作(PPP)機制已有經驗和信心,應當及早決策出臺新一輪大手筆安排,政府可僅以占小頭的資金“四兩撥千斤”式拉動企業、社會資金一起做。
二是2018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幅顯著回落到5.4%的低位,值得特別警醒。以環保、疏解城市非核心功能、防范火災隱患、“軍隊不得經商”等正確原則卻簡單化地運動式關停企業、拆店鋪、打擊低端就業,是“自毀長城”的形式主義誤區,亟應改善(許多軍隊大院外墻的商鋪,完全可以采取委托機制,隔開其租金與具體軍隊單位的直接關聯)。中國宏觀全局的“去杠桿”調為“穩杠桿”完全必要,因為廣義貨幣(M2)與GDP之比雖居高,但與“間接金融為主”有密切關系。實際生活中從物價看生產價格指數(P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都是“既無通脹,又無通縮”狀態,防范金融風險是“防患未然”。防風險,防的是“系統性風險”,要防止“因防風險而自我封閉創新空間與發展空間而產生的風險”。
三是中國消費潛力確實巨大,但單方面強調消費而忽視投資,邏輯關系上屬于本末倒置,貿易戰中是太阿倒持,決不可取。消費是投資的目的與歸宿,但無有效投資支持的消費,便成了無源之水,必然枯竭。總之,以創新的機制擴張本土選擇性“有效投資”,應成為貿易摩擦升級新階段上我們“有所作為”的一大重點。除內部視角的這一重點之外,外部視角的重點,則是注重“多邊博弈”爭取一切可調動潛力和有利因素,去應對中美間的“雙邊博弈”。
推薦閱讀:《國際商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雙月刊)創刊于1987年,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主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主辦。h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